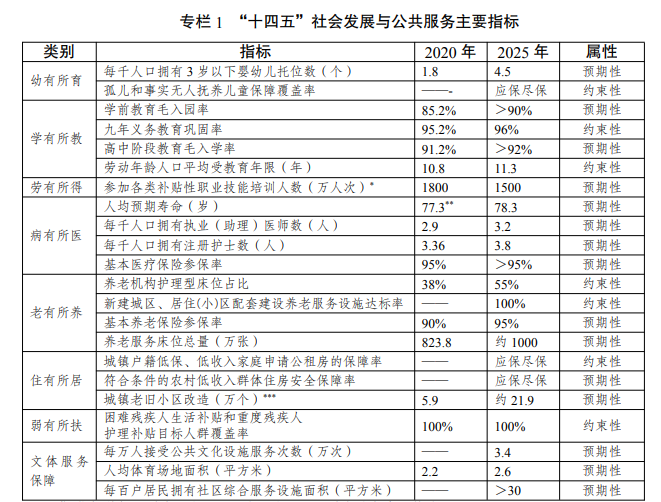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作者 | 尧七
二十年过去,人们仍然怀念张国荣。
明日(4月1日),香港红磡体育馆将举办张国荣逝世二十周年音乐会。音乐会门票于今年2月22日发售,不到两小时,门票已全部售罄。
随着张国荣生命的终结,他似乎已经远离人群很久,但每当4月1日的来临,我们总是会在浪潮般的追思中被提醒:他至今犹在,他从未远离。
2010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曾展开网络评选,推举出50年来的“全球乐坛偶像”,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迈克尔·杰克逊和the Beatles,位列其后的并非“猫王”或者麦当娜,而是张国荣。
作为全球性的文化偶像,他除了遗留下来大量音乐及影视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遗留下了一种迥异鲜明的性格特质,一种先锋的文化精神。
他以自身的存在告诉世人,真正的艺术家,难以被拘禁在一个刻板的框架之内。他们会不断跨越壁垒,在不同的规范之间流动,最终,拓宽人们想象力的边界。
百变的魅力
如果有人问,张国荣到底有何魅力使得他被惦念至今,我会首先推荐提问的人去看《热·情演唱会》。
这是张国荣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也是他被公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场演唱会。
2000年到2001年间,从红磡体育馆到世界巡回,张国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轰动。美国《时代杂志》在评价这场演唱会时,称它“Top in Passion and Fashion”,同时在激情与时尚层面臻于至美。
你可以在回顾这场演唱会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张国荣是如何打破男女性别的限制,让审美本身成为一场盛宴。
当年,在红馆的舞台上,他以天使的造型浮现于半空,纱幔中他面目模糊,但浑身披戴着洁白的光晕。唱起“当云漂浮半公分,是梦中的一生”时,他的声音像钟声响彻教堂。
在这场演唱会中,由法国时装设计大师让·保罗·高缇耶担纲张国荣的造型设计。
六套演出服,贯穿了“从天使到魔鬼”的主题。其中囊括了深V领大露背连体裤、美人鱼鳞片衫、贝壳裙裤、黑色透视装等一反男性常规的大胆装束。
同时,张国荣以长发造型亮相,他每一次将盘发散落之时,都意味着演唱会的又一次高潮来临。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张国荣在演唱《大热》之时。他身着剪裁合身的金属色西服,在红色的灯光下,通身闪闪发亮,他披散长发,当舞台的狂风从脚底掀起时,他的衣摆与发梢同时在空中纷飞飘扬。
随着演唱会的推进,天使堕落成魔,他脸上代表天使的泪滴也变换成眉心的恶魔符号,一切沉沦以他一袭红丝绒的恶魔造型宣告完结。最终,他换上白衣牛仔裤服装,所有面部的符号消隐,意味着他在解构天使恶魔的身份之后,重新回归“人”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他帅气地旋转把玩着话筒架,再看他随着音乐的节奏背过身去妖姣地摆动腰肢。人是很难不被他的美所震撼的。
同时,观众能够毫无障碍地意识到,这种美冲破了性别身份约束。它兼具刚烈与娇柔,涵盖坚强和脆弱,它变动不居,却又摄人心魄。
舞台上的张国荣,感染力十足
如果我们将张国荣在香港乐坛的告别(1989)和复出(1995)作为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看待,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出,张国荣复出乐坛后的音乐及舞台风格已经不再受到曾经偶像身份带来的禁锢,转而完全展露出他性格中的多元特质。
如果要追究这种变化的起因,那大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1989年在音乐事业的巅峰期宣布告别歌坛后,张国荣开始在银幕上大展光彩,《阿飞正传》《霸王别姬》《金枝玉叶》等作品让他再次蜚声国际。1995年他宣布回归乐坛,顶级艺术家的身份已成既定事实,他无需再向观众进行自身能力的确证。
张国荣在《金枝玉叶》中饰演著名音乐人顾家明
此时,他只需要作为一名先锋的艺术家,去进行文化前沿的开拓,而不再被逝去的辉煌局限其中。
服装造型,作为显示人类身份认同的符码,在这个时期不断地被张国荣运用到他的表演中。他正是通过这些符码的运用,不断地挑战并破除公众对于性别身份的刻板印象。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跨越97演唱会》上对歌曲《红》的演绎。
在这场演出中,张国荣涂上了红色的唇彩,在通身的黑衣黑裤之下,他穿上一双桃红色的珠片女士高跟鞋,与此同时,他还与一位赤裸上身的男性舞蹈演员合作,与之贴身跳起了性感的探戈。
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性别交织的状态。口红是女性常用的,但他的短发是男性常有的,红舞鞋是女性惯用的,但低沉有磁性的嗓音却是男性惯有的。它们共同显现出一种基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悖论,但又在审美的意义上达到了和谐。
在香港乐坛八九十年代的璀璨光辉早已变成历史余烬中的今时今日,我们再度回望当年,发现真正能够被人们广泛地记住并怀念的文化名人,仍是为数不多,而张国荣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张国荣
究其原因,或许可以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话来回答:“伟大的心灵都是雌雄同体的。”
而伍尔夫也曾经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强调过这番话的重要性,她说:“他的意思可能是,雌雄同体的头脑更易于共鸣和渗透;情感传递起来没有障碍;它天生就富有创造力,热情、完整。”
镜中的爱人
在《热·情演唱会》的尾声,张国荣已经完成从天使到魔鬼的身份过渡,最终回到了“人”本身,回到了他自己。
他穿着白色浴袍出现,要向歌迷们献上他这个夜晚最后的歌,《我》。在音乐声响起之前,他对所有人说:“其实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整个的主题就是,人要懂得怎样去爱人之外,最重要的是懂得去欣赏你自己——我。”
对自己的欣赏,或者更通俗一点说,自恋,几乎是在分析张国荣艺术成就时最恰当不过的切入点。
他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自恋的人,去上海做访谈时,谈到为什么想要去上海,他会说,因为知道上海是非常漂亮的城市,同时自己也是很漂亮的人,所以“非常配”。
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恋这个特质,去理解张国荣为何能够在性别的光谱之间无拘无束地流动。
如果说男性与女性在光谱中分列两极,各自有着特性,也不断相互吸引,那么张国荣所处的位置就是中间地带。他同时集合男女两性的美好之处,因而他可以爱任何一方,也可以无需对任何一方产生特别的爱慕。他只需要做自己,同时只需要爱自己。
这种对自身的省察和爱慕,在张国荣身上常常表现为一种壮丽的忧悒。
韩炳哲曾在《爱欲之死》中论述过自恋,他说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而忧郁症也是一种由自恋引起的病症,这种自恋会将人折磨到筋疲力尽,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诚然,自恋会带来忧郁,会带来壮丽的迷失,但是从艺术审美层面来看,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内在于人类精神中的自我垂怜的力量,同时能够增进人对自身美好特性的体认,并且能够对美好特性做进一步的激发。
在张国荣留下的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得以充分享受并解读这种自恋特性带来的美学意义。
电影《胭脂扣》片段
1990年,《阿飞正传》上映,张国荣在其中饰演旭仔,由于旭仔成长过程中生母缺席,因此在成年后对遇到的每个女人都表现得放荡不羁,但他其实始终没有真正爱上她们的能力,同时始终受到孤独感和无能为力的困扰。
其中流传至今的一个经典片段,就是旭仔在房间里对镜独舞的画面。
他独自一人,播放着拉丁舞曲《Maria Elena》,穿着白色背心和短裤,在夏日溽暑中扭动身体,陶醉起舞。他会注视着镜中自己的身体,凝视自己的面容和动作,进而沉浸在这个只有自我的世界之中。
电影《阿飞正传》片段
镜子,是自恋之人凝视自身的媒介,通过对自己的不断打量,他们会陷入强烈的迷醉,或者反之,陷入强烈的自我厌弃。总之,镜子是一个典型的意象,能够使得照镜的人和观众共同找到一条通向角色和观众内心的道路。
而这一典型意象,也常常被各个导演应用到对张国荣表演的捕捉中。
其中就包括《枪王》,彭奕行拔枪对镜,企图自我处决时情绪崩溃;《胭脂扣》开场,如花和十二少在墙上诸多镜子里初露缱绻;亦或是《霸王别姬》的尾章,程蝶衣独自对镜怀想。
程蝶衣,这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京剧名伶角色,据作家李碧华所说,是为张国荣量身订造。抛开程蝶衣性倒错的特质不谈,我想李碧华在比照着张国荣去塑造程蝶衣的角色时,已经看透了张国荣沉醉于自我爱慕的本质。
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饰演程蝶衣
张国荣在后来谈及对程蝶衣的理解时曾说:“程蝶衣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在艺术上,他们上台了之后,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我自己在演唱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拍电影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
程蝶衣之死,其实已经背离了李碧华原著小说中的结局,是出演“霸王”的张丰毅和出演“虞姬”的张国荣共同构想出了程蝶衣的自杀。
在张国荣对此的解释中,他提到,程蝶衣的自杀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虞姬”个性执着,要死在霸王面前;其二,是程蝶衣想要以自杀的方式来完成原著故事的情节,演一场真正的“霸王别姬”;其三,则是程蝶衣无法接受年华老去,因而选择自杀。
这三层原因,无论是哪一层,其实都涉及到如何处理角色内心和现实关系的问题。
电影《霸王别姬》截图
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程蝶衣其实从始至终都更爱自己,他所爱的段小楼也只是满足了他自身对爱的想象而已。而程蝶衣的悲剧在于,他被迫倒错了性别,因此,他沉浸的那个属于自我的世界其实根本不属于程蝶衣,而属于虚构故事中的“虞姬”。
当有关“虞姬”的虚构世界走向破灭的时候,程蝶衣自然也很难继续存在。死亡早已注定。
无脚鸟传说
在《阿飞正传》中,旭仔对镜独舞时,出现了全片最为经典的一段旁白——
“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飞呀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儿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
如今看来,张国荣自己就很像这传说中的无脚鸟,从精神层面来讲,他是从没有着陆过的。导演陈可辛也曾说,他觉得张国荣很不“人”,“你会觉得他不是平凡的人,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仙。”
在张国荣的生命里,如果说有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不断往前飞的话,那我想,应该就是反叛的力量。在他落地之前,这种反叛的力量几乎从未中断。
事实上,张国荣生前曾受到的对待,远不如现今这样充满尊重和推崇。反对和嘲讽的声音,几乎伴随了他演艺生涯的每个阶段。而我认为,他身上最具教育意义的特点就在于,他对外界戏弄的声音始终抱有一种反叛的精神,从不真正因为他人的冷嘲热讽而放弃自身对艺术事业的追求。
电影《春光乍泄》片段
1989年,也就是他宣布告别歌坛的这一年,在综艺节目《今夜不设防》中,张国荣曾经道出三段让他感到非常受伤害的经历。
其中之一的具体内容是,张国荣早期在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前身)出道后,曾有次在沙田做演出,由于造型太大胆和前卫,很不受观众待见。
当时,男明星在台上唱歌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但他却剃了光头,戴着海军帽上台演出。唱完后,他把帽子脱下来向台下飞去,却只得到一片嘘声。转身过来,发现又有一顶帽子被观众飞回来,“啊,怎么有顶帽子飞上台来,这么脸熟的,原来是自己的。”
综艺《今夜不设防》截图
“事情还没完呀。回到家去,那时候已经有些人认识我,知道我家里电话,回家查电话录音的时候,那些人就留了言,‘你收档啦,麻烦你再多读点书吧,你怕不怕不好意思的’,哇,真是,当时很hurt(受伤害)呀,哭了很久。”
但他紧接着坦陈自己为何能够坚持到后来,“后来我想通了,没有人可以让我没办法干下去,如果我真的不干这行的话,那是我自己光荣地走出来。”
他就像在《默默向上游》里唱的那样,在贡献着一种最为朴素的人生哲学,即,当他人不愿意正眼看你的时候,你要自己好好努力,“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重头”“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此后几年,张国荣的事业渐起。1984年,一首《Monica》让他红遍大街小巷,从此开始进入主流视野。这种热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致巅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告别歌坛,做到了他所说的,“光荣地走出来”。
但实际上,是是非非从来没有断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发生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举办之时。
彼时的香港媒体,不断用“玩低V贞子Look”“鬼影幢幢”“发姣露底(发姣在粤语中指女性卖弄风骚)”“自摸”之类的字眼来抹黑和丑化张国荣的舞台形象。
让·保罗·高缇耶,是张国荣好不容易请来的造型设计师,早在80年代,高缇耶已经率先开始让男人着裙装,他的设计往往意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让男装也能在阳刚的同时透露阴柔,反之亦然。
但在高缇耶得知香港媒体对张国荣造型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之后,他愤怒地表示,从此不再为香港的歌手设计服装。
香港媒体攻击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此,更严重的是,张国荣在马来西亚和大陆的演出被要求做出修改,使得他咆哮出口:“好!什么都可以改,唱回旧歌,穿回旧衫都可以,不过这已经不是我张国荣的show了。”
纵然如此,他仍然没有改变自身的选择和立场,在艺术上求取进步的强烈渴望始终驱动着他。在公开对媒体的攻击做出回应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这只能表现着香港有某一部分的传媒肤浅的一面,我觉得有时,做到我们这个级别的艺人,只可以再做些trends-setting,就是创先河的东西。”
吊诡的是,当张国荣开启全球巡演,将同样的演出带到世界各地并且引发了热烈的回响之时,媒体的报道又开始转为刊登许多溢美之词。在香港民众的强烈呼声之下,2001年,张国荣又在红馆加开了六场《热·情演唱会》。
我们始终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因素引发了张国荣长达一年的生理性抑郁,并最终造成了他的死亡。或许他自己也回答不了,以至于在遗言中仍旧要问:“我一生冇(没有)做坏事,为何这样?”
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结果: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24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碧华曾在怀念张国荣的文章里写:“这天我特别痛恨在文华酒店门外,撞毁的铁栏下(你的身体竟硬生生把坚牢的金属拗曲了),一个陌生人,用凶猛的水柱把你遗留的一大滩血,连同洒落的红花,不消一阵,冲洗净尽。你随水而去,转瞬不见了。”
如同她写的那样,后来,你在烈火中大去。
自你在烈火中大去,至今,已二十年了,彼岸可好?你可能还不知,自你走后,此岸的追忆,从未断绝。
张国荣在《纵横四海》里的经典画面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