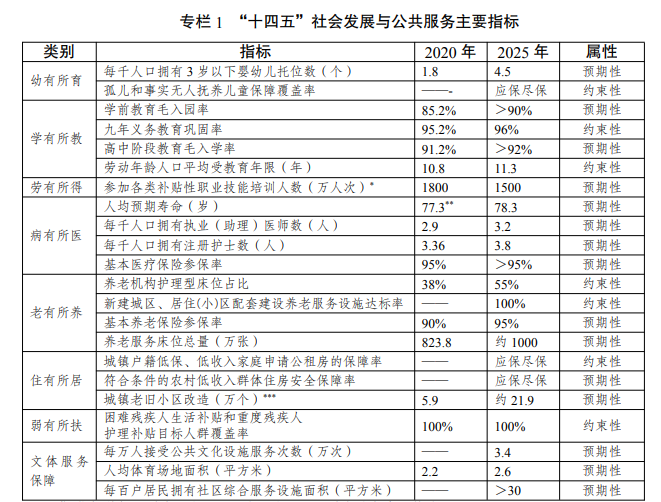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资料图】
【资料图】
我将【新实在论】总结为这样三个关键词——存在论、批评、启蒙,其分别回应后现代主义的各个谬误:存在-知识谬误、勘定(ascertainment)-接受谬误、知识-权力谬误。
本体论简单地意味着:世界有它的规律并强加它们【于我们】,也就是说,它不是这样的温顺的殖民地,【我们】在其上行使概念图式的建构性行动。后现代思想家在这里犯的错误是由于存在-知识谬误,即混淆存在论和知识论:混淆所存在的东西和我们关于所存在的东西所知道的东西。清楚的是,为了知道水是H2O,我需要语言、图式和范畴。但是,水是H2O完全独立于我的任何知识——以至于即使在化学诞生之前,水也是H2O,且如果我们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它仍将是。大多数情况下,就非科学性的经验而言,水潮湿,火燃烧,不管我知道与否,独立于语言、图式和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有东西抵抗着(resists)我们。它就是我所说的“不可修正性(unamendability)”:实在的突出特征。这当然可能是一种限制,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支持,其让我们能区分梦与现实、科学与魔法。这就是为什么我把献给存在论的章节命名为“实在论”。
因而,批评意味着如下之点。伴随着我所定义为“勘定-接受谬误”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假定勘定现实包含了接受现存的事态,且相反地(尽管带有逻辑缺口),非实在论本身就是解放性的。然而,它显然并非如此。实在论是批评的前提,而非实在论则一致于默从(acquiescence),那个我们讲给孩子以便他们睡着的故事。波德莱尔指出,一个花花公子只可能对人群说话以嘲弄他们。更不用说一个非实在论者了,他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能力确定他是否在真实地改变他自己和世界,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否只是在想象或梦想做着一些那一类的事情。而实在论者则拥有批评(如果她想要)和改变(如果她能够)的可能性,理由与“为何诊断是治疗的前提”的平凡理由相同。又鉴于任何以自身为终点的解构都是不负责任,我决定将第三章命名为“重构”。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启蒙。最近的历史证实了哈贝马斯的这样的诊断,其在三十年前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这样一股反启蒙的浪潮,其在我所定义为“知识-权力谬误”的东西中找到了其合法性,根据这一谬误,在任何形式的知识背后都隐藏着一种被经验为否定性的权力。作为一个结论,知识变成了一种奴役的工具,而非主要将自身与解放相联系。这种反启蒙是现代性之黑暗(darkness of modernity)的核心:即,(在例如德·迈斯特、多诺索·科尔特斯、尼采的伟大思想家们那里的)对进步的观念、和对知识与解放之间联系的信任的拒绝,其在波德莱尔的“王座和祭坛”是一则革命格言的想法中得到了总结。后现代主义-民粹主义的时间差似乎使他们被证明为正确的。现在,为了走出这种深深的蒙昧,并获得最后一章所借以命名的“解放”,就有必要求助于启蒙,其,正如康德所说,是“勇于运用理智!”,且标志着“人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的摆脱”。今天,启蒙仍然需要一种对这样的人类的立场和信仰,其不是一个需要救赎的堕落种族,而是这样一个动物物种,其不断进化并在其进步之中被赋予了理性。